热门关键词:


(我在深圳住公租房:房租900,6年没涨价)
PART01
“什么时候能住上像样的房子?”
熊琳敏锐地意识到,自己被跟踪了。
她走一步,对方停一步,脚步声窸窣,感觉越来越近。回到家还要经过一段小巷,没有路灯,黑漆漆的,“经常听到女生在城中村被跟踪,超级害怕。”
幸好有家小吃店还没关门,她马上拐了进去。20分钟后,那名陌生男子才离开。
一摸额头,全是汗。
经历这次尾随后,她火速搬家,这已经来深四年里的第四次了。
理由总是不尽相同——房租太高,环境不好,通勤时间太长,总之,一处住的舒心都没有。
频繁的搬家,让熊琳有种极度的不稳定感,她总觉得自己像个浮萍,飘来飘去,什么地方都驻扎不久。
和许多“深漂”一样,熊琳对自己房子有着具体的想象:大大的落地窗,可以照进阳光;
阳台也要大些,她热爱园艺,能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。厨房也不能太小,周末朋友来了,可以做顿好吃的。
当然,还要有个衣帽间,四季的衣服都能挂起来,不用皱巴巴地塞进柜子里。
只是,幻想落到现实,熊琳不知道还要有多久。
2016年,徐艳进入了公租房的轮候库,对她来说,在深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
丈夫在印刷厂工作,一个月收入七八千,自己拿着2000块最低工资,住进城中村。
房子只有十平,厨房和厕所在一起,想要解手,“先憋着,等我炒完菜”。厨房里装不了抽风机,只有排气扇,一到夏天,就是“人间炼狱”。
徐艳曾经的住所
女儿出生后,徐艳架了一层阁楼,夏天铺一层薄的床垫,底下就是木板,特别硬,“硌得人生疼”。
一到晚上,老鼠和蟑螂横行,没睡过一个好觉。
我向她索要一些以前出租屋的照片,“没有啊,那么烂的房子,谁会愿意照相?”
在城中村,大家都认识徐艳,她爱交际,男女老少,见谁都能聊上几句。
但相熟的人那么多,谁都没去过她家,“不好意思让别人来家里,根本没地方坐”。
只有偶然的一次,她在家附近碰到了嫂子的同学,对方执意要去家里坐坐。
徐艳带着她穿过狭窄的楼梯,走进昏暗无边的长廊,黑暗得像鬼片里的事发地,坐在烂掉的沙发上,对方蹦出了一句话:
“你在深圳这样活着,有什么意思?”
徐艳住所外景
徐艳经常会买几张两三块的彩票,梦想着有一天中了奖,可以脱离这个逼仄的空间,买个大房子,舒服地过日子。
熊琳和她都在想:这样的时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?
PART02
留不下,回不去
如果没有住进公租房,许明深可能就离开深圳了。
在深圳的八年,他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摇摆的状态,回去还是留下,这个问题问了自己很多遍。
刚来深圳时,看着几何形的高楼大厦,许明深觉得是另一个世界。在老家,房子最高也就10楼,开车两个小时就能逛完整个市区。
自由和平等的机会,也是老家所没有的。
许明深是大专学历,专业是计算机,最开始,他在软件园的一家公司写代码,公司虽小,但接触到的同事都是本科学历,甚至还有的。
“当时我有点自卑,觉得跟他们插不上话。”但相处久了,他发现同事们都很热心,在工作上遇到问题,大家都特别乐意解答,还会分享一些Java和C语言的课程,完全没有学历上的优越感。
公司也不是唯学历论,“谁技术好,谁就能拿多钱”,这让初来深圳的他,接收到一个积极的讯号:无论你是什么背景,只要有能力,就能被重用。
现在,他已经在一家中型公司做技术管理,自己带一个团队,开发了很多不错的产品。
回溯迄今的职业生涯,许明深觉得这在老家是不可想象的。“在老家,可能就是喝茶看报,生活像一潭死水。”
但无论他多想留在深圳,现实也是残酷的,自己眼看着租住的小区,房价从两万涨到了七万,“再怎么拼命,厕所也买不起呀。”
留不下,回不去,许明深陷入了焦灼。
徐艳的焦灼,藏在一架钢琴里,这也是她留下来的答案。
在城中村住的时候,一到晚上6点,外面收垃圾的人在捶铁皮,肖邦的《激流》就在屋内响起,徐艳站在女儿旁边,紧盯着琴键。
小学的时候,班上的同学都在学才艺,徐艳也憋了一股气,“不能让女儿落下。”钢琴的牌子是拉姆特,花了一万二买回来,学费一个月就要800。
徐艳和丈夫都是高中学历,对于女儿,她希望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,“至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”。
钢琴之外,课外补习一年就要三万。初三那会,她在学校旁边租了房,上午干家政,中午赶回去给女儿做饭。
钱都是死命抠出来的。除了省去的房租,徐艳的衣服没一件超过100块,家里的器具基本都是二手。她做了六年的家政,早上8点到晚上8点,一个月五千。
朋友们都觉得徐艳太能熬,为了孩子,真的太苦了。她也不是没动摇过,老家有房子,物价又低,找个工作三四千,日子怎么过都快活。
“我女儿在这里生活惯了,回老家,到最后毕业还不是来深圳打工?”
从孩子出生到现在,徐艳在暗黑的屋子里熬了二十年,熬出了一身风湿病。屋子照不进阳光,养过的植物基本没几天就死了。
2020年,女儿考上了深圳的一座大学。她觉得像是熬了一锅很久的汤,终于尝到入口回甘的快乐。
PART03
美好生活的希望
熊琳终于不用担心被尾随了。
2016年,她住进了公租房,理想中的房子正在50平的空间里实现。落地窗不大,但早晨一进客厅,就能看见阳光洒在地面上。
两室的另外一间被她打造成了衣帽间,衣服终于可以整齐地挂起来,没有褶皱。
阳台上也种上了多肉,一排排摆在那,终于有点像样的园艺了。
熊琳最喜欢的一件家具是星星窗帘,到了中午,阳光投射在窗帘上,闪着光斑,“感觉就是属于自己的世界”。
属于自己的,不仅是空间,还有切实的稳定感。
6年前搬进来到现在,房租从来没涨过,一直就是900多,再也不用担心被房东赶走,“只要你不买房,基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。”
当然,还有最重要的归属感。
归属感这个词是抽象的,它在生活的细节里得以显现。熊琳的邻居是一家五口,平时做了饭会叫她过去吃,从老家回来,也会专门给她带份特产。
归属感也意味着一份依靠。一次,熊琳犯了胃病,疼得不行,她试探性地问了楼上的大姐,对方马上下楼来接她。
这些在出租屋,都是不可能发生的。“跟舍友不会有任何交流,各过各的”。
小区附近的配套设施在不断完善,医院、超市、学校都在一点点建起来。
家里水管煤气坏了,跟物业一说,马上就有人上门来看,“甚至比商品房的小区还要好。”
住进来的第一个春节,小区挂满了红灯笼,熊琳心里暖洋洋的,“第一次在深圳有家的感觉”。
熊琳的公租房
房子带来的稳定,也意味着拥有展开新阶段的勇气。
许明深申请到了安居房,两室一厅,同类型的房子市场价要4万多。
安居房的价格低于市场的一半,首付只要30多万。
以前他交过几个女朋友,都因为房子的事无疾而终。他也理解,35岁无房,哪个女孩也不愿跟着他受苦。
通知选房的那天,长久以来的摇摆感终于消失。许明深在空荡的屋子里,感到模糊的未来在变得清晰:
省下来的钱可以买辆车;有了孩子,不用担心上学的问题,附近有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,跟学区房的家庭一样,积分入学。
一切都在变好。
一个月前,徐艳完成了一次“大迁徙”,那台钢琴,也跟着来到了光明。
几天前,我去了她的新家,面积是原来的六倍,宽敞明亮,那些在城中村种不活的花草,正在这里蓬勃地生长着。
徐艳新家
她指着阳台对面的灰色高楼,“按照对面卖的价格,我这个房子也要四百多万。”随后咧嘴笑了笑,又蹦出一句,“没想到我也能住上几百万的房子。”
住在公租房的第一晚,她和丈夫激动得失眠,跟做梦一样,床垫软软的,和阁楼里的硬木板相比,一点也不真实。
也许出于这种不真实,在厨房忙碌的她,还时不时转头问我,“房子三年一签,到时候是不是又把我们赶出去?”
阳台的绿萝、独立的卫浴、桃木做的衣柜——尽管心里藏着焦虑,眼前的生活,也足以消解。
坐电梯的时候,她兴奋地跟我说,“你看,这电梯里都有空调呢!”
对于孩子,居住环境的改变,也在心里掀起波澜。
住在城中村的时候,女儿很少邀请同学来家里。后来有同学来家里吃饭,回去就问她,“你怎么住这么破的房子啊?”
偶尔有朋友来,女儿也不是很不情愿,“能不能在外面吃?”
徐艳知道因为房子,女儿有点自卑,孩子从未发过朋友圈,她一度以为被屏蔽了。
直到搬家后的第二个周末,她刷到了女儿的动态,只有简单的两个字:
回家。
聊起这件事时,已经是晚上8点,桌上摆满了菜,还开了一瓶白葡萄酒。我们举起了酒杯,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
说完“一切平安健康”,徐艳抿了一小口,嘴角勾起了一点笑意,身靠墙壁,她似乎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。
//
在深圳经常有人打趣,有户口不算是深圳人,有房子才是。
作为惠民项目的安居房和公租房,不乏一些吐槽声音:轮候时间长、房源区位比较偏……但不可否认的是,很多和徐艳、许明深、熊琳境遇相近的深漂家庭或者年轻人,因此获得了一份确切的稳定感和归属感。
离开还是留下,或许很多人都在思考。而安居房和公租房的持续推行,无疑给了希望留下但又觉得买房无望的人,一个可触及的盼头。
令人感到欣慰的是,深圳政府已经在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步伐。
根据深圳住建局官网提供的信息,2019-2020年,深圳市开工筹集的安居工程项目共303个,共计套。
在徐艳家的楼顶,对面是整齐划一的白色楼房,黄色的起重机正在旋转,那是即将建成的另一个安居项目。
夕阳的余晖抛洒在建筑上,我们都感觉到,某种希望正在远方升起,路途虽曲折,但不再是看不到尽头。
备注:文章人物均为化名。
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本文由原创发布
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扫描上面二维码,微信咨询
落户咨询热线:133-7767-2635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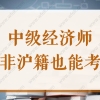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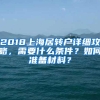








咨询热线
133-7767-26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