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门关键词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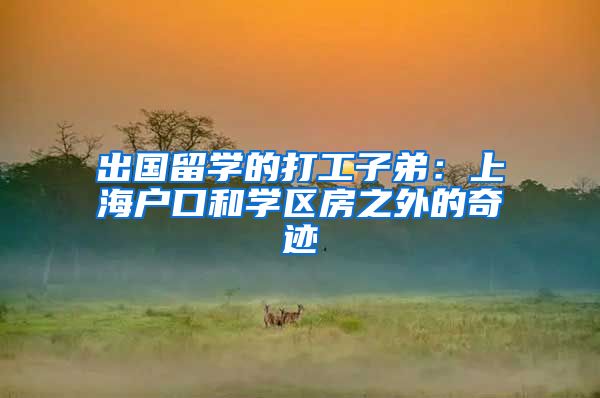
(出国留学的打工子弟:上海户口和学区房之外的奇迹)

 喜欢音乐和绘画的星晴,人生梦想之一就是用绘本给小朋友讲故事
喜欢音乐和绘画的星晴,人生梦想之一就是用绘本给小朋友讲故事
星月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了八年,高中两年,大学四年,以及工作后的两年。温哥华这座城市有着令她喜爱的气质:繁华与宁静并存。白天去城市中心上班,便走入了喧嚣与热闹;晚上下班后回到住宅区,又回归了平静安宁。
如今竟在温哥华这么多年了,她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就在八年前,她还是上海一所民办职高的学生,没有上海户口,不能参加中考、高考,上不了大学,前途一片渺茫。她常常回家晃荡,不去上学,对世界失望。唯一有兴趣的,就是缠着妈妈要钱,想去做生意,像好友家一样去卖水果。
那时她万万不会想到,自己有一天会拿到全额奖学金,去加拿大念高中、大学,毕业后在那边工作。还有她的弟弟恩四、妹妹星睛,也都拿到全奖出去读书,如今在美国念大学。
这是一个惊奇故事。他们,还有许多在上海东北角成长起来的打工子弟,构成了这个故事神奇的一部分。他们没有上海户口,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、高考。但如今,却从他们中走出了10个拿着奖学金去国外留学、工作的学生。
在这个教育越来越难改变命运的时代,无数家庭被卷入学区房、补习班、兴趣班的比拼之中,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跨越了政策、阶层、资源匮乏的藩篱,另辟蹊径,去了国外留学?他们的人生,是否因此不同?
1
汽车在温哥华海边的田园小道上行驶,像是穿越了一座森林,最后停在一处靠海的房子前面。一位老爷爷倚在门前,面露微笑,等待三位学生的到来。几只小鹿在路边吃草,有人到来也不受惊吓,兀自安祥地啃噬草地。夜已深,抬头便可见漫天的繁星,连银河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那是星月抵达温哥华第一天所目睹的场景,她和两位同学下飞机后被送到海边的本地人家中,寄宿三天,度过初抵异国的缓冲期,迎接三天后UWC(世界联合学院)加拿大分校的开学典礼。
三天后,从住家爷爷家里搬去学校,她再次被这所魔法般的校园给惊呆了:“那是一个连大门都没有的学校。几座木头房子零星地散落在森林里,学校的一边是森林,另一边是大海。小鹿在草地上吃草,小浣熊在树枝上睡觉。”她无法相信,这就是自己将要度过两年高中生涯的地方。
就在半年多以前,她还在上海吴凇的民办职高里茫然不知所终。转折来得太过突然,连她自己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想: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?
她想起了半年前的冬天,那个决定性时刻。
那是2011年1月,她从上海去了北京面试。全英文面试,参与竞争的都是和她差不多大的中学生。他们大多来自国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,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只有她是中专生。
过年的时候,一个在复旦学习人类学的挪威人吴郎来帮她练习英语口语,在她家住了十几天。但她每天带着他去附近的河沟里钓鱼钓虾,在家里弹吉他唱歌。妈妈被气得不行,不是说练英语吗,这丫头怎么一点儿也不用功?那时候,妈妈说了好多气话:“你要能考上啊,我就给全上海每条狗都缝件衣服,头朝下走路。”
但她知道,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,看似在玩,实则也是在生活中去练习和思考。面试那天,英语交流不算太吃力,偶有不会的单词,也能想办法换个词表达。重要的,是把自己怎么想的说清楚。
“如果你是中国政府官员,你要做什么?”面试官赵宾问她。
“我要改变中国的户口。”她说。他们就中国的户籍制度讨论了一番,赵宾又问:“去了国外你想做什么?”
“想做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,改变中国教育现状。”
“怎么改?”
“我要拍记录片,让大家去看,在看的过程中改变人们的想法。”
赵宾眼前一亮。他是UWC校友,彼时担任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,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。他面试过很多人,很多人都很懂得面试技巧,答案早就设计好了。但星月的回答,他感觉得到是发自内心,她眼睛里的火花更是无法设计。
“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,一看就知道是会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、很有能量的人。”赵宾说,那些年面试的人里,这样的人不超过5个。
2
那之前的星月,是上海郊区一所民办职高的高二学生,前途未卜。她原本也可以拥有光明的未来:初中时成绩优异,经常考全校第一,每学期能拿2800块奖学金。只要能参加中考、高考,考上一所好大学毫无问题。
但一切前景在她初二的某天被击碎了。那一天,老师和她确认,她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。星月妈妈王秀的头发是从那一天开始白的。“家里三个小孩,老家回不去了,上海又不能考试,可怎么办呀?”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,成天往区教育局跑,哭诉,求告。但政策的大门之下,个体的努力却像蚍蜉撼树。
星月也回不了老家。小学五年级时,她曾被送回安徽老家读了一年,成了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。那一年,她在听不懂的方言环境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,还带着班里同学逃课玩耍,屡屡被老师告家长。王秀不得不把她接回上海,那也是王秀第一次意识到:孩子一定要带在身边,陪伴他们成长,错过了那些年孩子长歪了,就再也无法挽回了。从那以后,她再没想过把几个小孩送回老家。
可到底该怎么办呢?妹妹星晴记得,当时“所有人都很有危机感,初中毕业后就没书读了,到时该怎么办?”文艺才能突出的星晴,曾想过种种办法,甚至找到了一条出路:去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特长生。在招生简章里,她看到了格外醒目的字眼:只要才艺出众,可以不受户籍限制,破格录取。
但最终,她因一年十几万的费用泄了气。父亲的集装箱物流生意出了事,母亲也因此去外国人家里带小孩……养育三个小孩的他们,无法支付这高昂学费。
一夜之间白头的王秀,又去找张轶超商量三个孩子的未来。多年来,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张老师帮他们解决了很多小孩上学的问题,他为了帮助这些农民工子弟而成立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,也成了国权北路一带农民工孩子的另一个家。
2001年,还在复旦念哲学系研究生的张轶超第一次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,被那里的环境惊呆了。在那片到处是简易房的棚户区,几间简陋的房子就构成了学校,一群浑身灰扑扑的小孩子挤在里面上课。
他不敢相信,在离安静优雅的复旦校园不到五公里的地方,竟然还有这样简陋的小学课堂,课堂上的老师没有专业教育背景,甚至还有中学毕业生。
张轶超决定在复旦组建志愿者团队,去给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们上课。五年后,他把短暂零散的支教,变成了有固定场所和内容的公益教育事业久牵,为这些孩子提供课外的音乐、艺术、英语等课程,志愿者老师来自附近的复旦、在上海工作的白领,还有张轶超本职工作所在的上海平和国际学校。
星月是最早进入久牵的学生之一。她的童年都留下了张轶超带来的快乐和明亮,踏青、抓蝴蝶、制标本、钓鱼虾、弹吉他、唱歌,小年夜在国权北路的棚户区里放烟花,夏日的夜晚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。
这个成天在棚户区晃的青年人,后来成为星月和弟弟妹妹去往UWC的关键人物。
 给久牵的孩子们上课的张轶超
给久牵的孩子们上课的张轶超
3
张轶超也很愁,那么优秀的学生,就真的与大学无缘吗?
直到2010年的冬天转机出现。那时,朋友知道他在做久牵,告诉他有一所名叫UWC的国际学校,准备在中国开放招生。
UWC,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,由德国教育家库尔特·哈恩于1962年创立,意在将不同国度、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,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,为各自的社区和世界带来改变。彼时共有14所学院,分布在世界各地,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。它提供两年大学预科教育,之后可以申请海外大学。
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,其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,毕业生中不乏外交部副部长等人。直到2010年,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,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学生。
得知这一切后,张轶超立刻组织了几个符合UWC招生年龄的孩子,集训英语,填写申请书。星月她最初是不抱希望的,全国范围内只招25名学生,得有多渺茫啊。快到报名截止日了,她连申请书都没填,是张轶超在截止日前三天逼着她填完后寄了出去。
那一年,星月成了唯一一个进入面试并被录取的久牵学生。
王秀是在4月1日那天接到电话得知结果的,当时的场景她至今记得一清二楚:
“愚人节那天,她给我打电话,妈妈我被录取了,你猜我考到哪里去了?加拿大,最好的UWC,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
我简直不相信,一看手机愚人节,这死丫头,愚弄我。电话一挂,我把手机装包里不理她。一会儿张老师打来了,星月妈妈,星月有没有给你打电话,她被录了,最高分数录取。
那我高兴得失控了,在公交车上哭了,我说张老师真的谢谢你,没有你一步一步给我们安排,我们也走不出去。”
星月也为所有久牵的学生打开了一扇门。2011年后,每年都会有六七个久牵学生申请UWC,平均每年被录取一个。几年后,恩四和星晴也相继被UWC全奖录取。
上海姑娘彭洁云曾在久牵做了两年志愿者,教小提琴,她带的好几个小孩都出了国,她至今对他们印象深刻:
“她们眼睛里是有光的,很有灵气,学什么东西都很快,知道自己要什么。都很忙,在久牵上很多课,还有的在做实习,或者考雅思,去支教,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。”她说,“相比于上海本地学生,他们更有危机感。而且他们在久牵接触的人和事很丰富,复旦校友、上海很多企业的公益活动都是和久牵对接,让这些学生视野很开阔。这一点,甚至比很多整天忙着学习的本地小孩要强。”
4
但去了UWC并不是故事的终点,而是另一种喜忧参半人生的开始:几乎所有久牵的学生在UWC第一学期都想过退学。
在加拿大的第一个月,星月很难熬。在异国他乡,人们用英语聊天、上课、做作业,她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全英文环境,上课像是在听天书。巨大的压力一度让她很难承受,但她却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回家,因为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艰难与脆弱。
恩四和星晴也经历了最初的文化和语言冲击,以及课业的艰难。他们在各自的学校里,看到每学期末都会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而退学。
周贝贝是去年刚考入UWC的久牵学生。她17岁,在UWC常熟分校念了一年预备班后,即将去亚美尼亚分校。过去一年,即便是在位于中国的分校念书,她也感觉遭遇了“毁灭性打击”。在上海公立中学念初中的时候,她的英语成绩很好。但来到国际学校,所有课程、作业都是英语,用英语写剧本、演话剧、做报告,她感到压力巨大,一度感到很消极。
可是,他们身上又有种韧性,就像开在山野的蔷薇,在野外无人照看也会猛烈生长。
八年前在加拿大的星月,最艰难的时候常坐在学校海边的甲板上看着边上一棵树,觉得自己就像在爬树一样,人还在树下艰难挣扎,但好想有一天能够爬到树顶看上面的风景。在那一刻,她意识到“人要直面自己的弱点才能变得更强大”。从此,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成了目标,不管行不行,都先报名。
那之后,她在例行会议上发言紧张到死也要说,在音乐节上去表演节目,和同学们彻夜聊世界、聊梦想,接受物理老师的徒步挑战,跟校长理论为什么要取消她最爱的人类学课程,为了练习跳海差点被淹死,和日本同学讨论中日战争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以微笑和拥抱结束……
两年后从UWC毕业时,她哭得像个泪人,学校的老师同学就像家人一样亲切,自己也在一次次自我否定、肯定之间,不断走出舒适区,变得更强大坚强。后来,她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全奖,念人类学和经济学。
四年后,星晴也从UWC毕业。极具语言天赋的她,去UWC之前就擅长英语、日语等几种语言,她的UWC两年也更平顺。毕业后,她和恩四一样,拿到全奖去了美国念大学。
 大学里,恩四申请了海上学府项目,坐着游轮环游世界,在游轮和沿途各地学习
大学里,恩四申请了海上学府项目,坐着游轮环游世界,在游轮和沿途各地学习
周贝贝熬过了第一年,她感到有些“心累”。在常熟UWC,她的同学多是家境优越、以考国外名牌大学为目标的典型国际学校学生,每个人都有一项“很优秀”的特长,辩论、演讲、组织策划、文学创作……她有时会遭到挑衅,被质疑英语水平和能力。但在极大的差距下,她仍然拼尽全力拿到了合格的分数,让所有人都惊叹她这一年极大的进步。
选择UWC亚美尼亚分校去读完两年正式课程,是一个面对巨大未知的决定,她仍对此感到忐忑,不知道前方是什么,也不知道两年后能否申请到心仪的大学。但她的身上始终散发出掩不住的活力,对远方的亚美尼亚,“保持挑战自我的初心,去探究更大的世界吧。”她说。
6
在金融机构工作一年后,星月终于跳槽去了教育行业,同时将在今年9月去加属哥伦比亚大学念教育学研究生。
她还是走到了教育这条路上来。2017年暑假,她在面临择业时,被UWC中国常熟分校共同创办人、哈佛上海中心执行董事王颐的一句话点醒了,他说:“你的背景就是教育,所以你做教育是理所当然。”
她意识到他是对的。“因为教育不平等我没法在上海中考、高考,不出意外也不能读大学;但也是因为教育我才有机会读UWC,才会大学毕业,并成为此时此刻的我,所以我是应该做教育的。“星月说。
冥冥之中,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会走到一条路上来。今年春天,同样是打工子弟、从北京蒲公英中学考到UWC的段孟宇,拿到了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,所学的专业也是教育。
张轶超也是在和这些孩子的接触中,发现了自己对教育的兴趣,从而在这条路上走了快20年。20年了,一边在国际学校教书,一边做久牵,他也从当初那个青涩、为了争取权益和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当面冲撞的年轻人,变成了一个1岁孩子的爸爸,两鬓的头发染上了零零星星的雪白。
早先,有朋友说张轶超你做久牵这事儿吧,改变不了这些孩子的命运,他们还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,但好处是他们成为坏人的概率变小了。“现在看,这些孩子都不坏嘛,普普通通的劳动者,留点善意在他们心中也是挺好的事儿。”张轶超说,“不上UWC又怎样呢?毕竟绝大多数孩子是上不了UWC的。”
从久牵走出来的大部分学生,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普通劳动者,中专毕业后找一个对口的工作。有的做平面设计,有的在游戏公司画图,或者再普通一点,在爸妈的水果摊上卖水果,在超市做收银员,这些都是在上海。回老家的,有在跑运输,也有人生了孩子做全职妈妈。
而去了UWC的学生,如今有两个从国外的大学毕业,留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,其余的都还在念书。他们去了英国、波黑、香港、加拿大、美国、亚美尼亚、德国,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和他们的父辈相比,他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。
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,或许也会成为普通人,不过是做着白领工作的普通人。但,那又怎样?
张轶超看到了另一位从事公益教育、帮助打工子弟的同仁写的文章,文章里说希望这些孩子今后能“做珍贵的普通人”,他很赞同,却觉得这样还不够。他觉得教育还有一点很重要:它必须得给人力量。
“如果教育不能让人变得强大,那么你要教育干嘛呢?我可以做珍贵的普通人,但当选择来临的时候,我必须有力量去捍卫珍视的东西。如果没有力量去捍卫珍视的东西的话,那做普通人有什么意义呢?”
 久牵的孩子们
久牵的孩子们
注:本文为腾讯旗下非虚构新闻账号“谷雨实验室”独家撰稿,为未删改原文,未经许可请勿转载。

扫描上面二维码,微信咨询
落户咨询热线:13671738356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咨询热线
13671738356